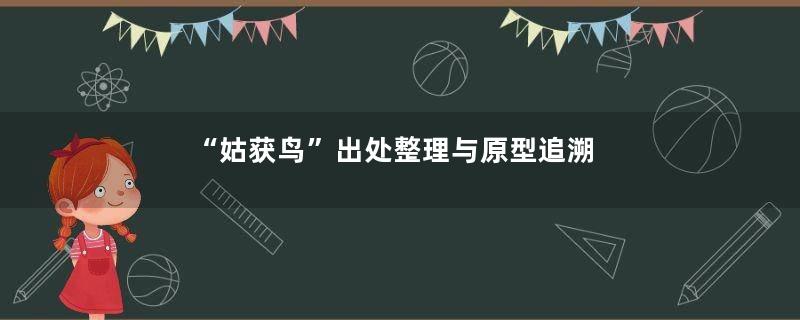
以鲁迅在《古小说钩沉》中对《玄中记》里姑获鸟一项的辑录依据为主要线索,在下面罗列一些个人在能力范围内找到的关于姑获鸟的记载:
0.《搜神记》(东晋·干宝著,约283~351年),取四库全书本
豫章新喻县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
1.《玄中记》(东晋·郭璞著,约276~324年)原本亡佚于宋明,取《古小说钩沉》辑本
姑获鸟夜飞昼藏,盖鬼神类。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钩星,一名隐飞。鸟无子,喜取人子养之,以为子。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今时至此,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为多。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今谓之鬼车。
2.《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约472~527年),取四库全书本
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阳新县之青湓山,西北流迳阳新县,故豫章之属县矣,地多女鸟。
《玄中记》曰:阳新男子于水次得之,遂与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间养儿不露其衣,言是鸟落尘于儿衣中,则令儿病,故亦谓之夜飞游女矣。
3.《荆楚岁时记》(南梁·宗懔著,约501~565年;隋·杜公瞻注,生卒不祥),取两江总督采进本
正月夜,多鬼鸟度,家家槌床打户,捩狗耳,灭灯烛以禳之。
按︰《玄中记》云,此鸟名姑获,一名天帝女,一名隐飞鸟,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女子养之。有小儿之家,即以血点其衣以为志,故世人名为鬼鸟,荆州弥多。斯言信矣。
4.《本草拾遗》禽部(唐·陈藏器著,约681~757年),取江户写本
姑获,能收人魂魄,今人一云乳母鸟,言产妇死变化作之。能取人之子,以为己子,胸前有两乳。《玄中记》云:姑获,一名天帝少女,一名隐飞,一名夜行游女。好取人小儿养之,有小子之家,则血点其衣为志。今时人小儿衣不欲夜露者,为此也。时人亦名鬼鸟。《荆楚岁时记》云:姑获,一名钩星,衣毛为鸟,脱毛为女。《左传》云:鸟鸣于毫社。注云:譩譆是也。《周礼》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夭鸟。即此鸟也。
5.《酉阳杂俎》卷十六·羽篇(唐·段成式著,约803~861年),取内府藏本
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曰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贻小儿不可露处,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
6.《北户录》卷一·孔雀媒(唐·段公路著,约869年),取两淮盐政采进本
雷罗数州,收孔雀雏,养之,使极驯扰致于山野间:以物绊足,傍施网罗,伺野孔雀至,即倒网掩之,举无遗者。或生折翠羽,以珠毛编为帘子、拂子之属,粲然可观,真神禽也。(又《后魏书》:龟兹国,孔雀群飞山谷间,人取养而食之,字乳如鸡鹜,其王家恒千馀只。)一说;孔雀不必疋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如白鶂,雄雌相视则孕。或曰:雄鸣上风,雌鸣下风亦孕。见《博物志》。(又淮南八公《相鹄经》曰:复百六十年变,止雌雄相视,目睛不转而孕,千六百年形定也。又《稽圣赋》“豪豕自为雌雄,缺鼻曾无牝牡”,即雌兔舐雄而孕是矣。)又《周书》曰:“成王时,方人献孔鸟。”方亦戎别名。《山海经》:南方孔鸟。郭璞注:孔雀也。《宋纪》曰:“孝武大明五年,有郡献白孔雀为瑞者。”噫!象以齿而焚,麝因香而死,今孔雀亦以羽毛为累,得不悲夫。
愚按:《说文》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字林》音由)。今猎师有囮也。《淮南万毕术》曰:“鸱鸺致鸟。”注云:“取鸱鸺,折其大羽,绊其两足,以为媒,张罗其旁,众鸟聚矣。”《博物志》又云:“鸺鹠(休留)鸟,一名鸱鸺。”昼日无所见,夜则目至明。《庄子》云:“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冥目而不见丘山。”言性殊也。人截手爪弃露地,此鸟夜至人家,拾取视之,则知有吉凶。凶者辄更鸣,其家有殃也。陈藏器引五行书:除手爪埋之户内,恐为此鸟所得。其鸺鹠,即姑获、玄车、鸮鵩类也。
姑获,《玄中记》云:“夜飞昼藏,一名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隐飞。好取人小儿食之。今时小儿之衣不欲夜露者,为此物爱以血点其衣为志,即取小儿也。”又云:“衣毛为鸟,脱毛为女人。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即藏之。即往就,诸鸟各走,取毛衣飞去。一鸟独不去,男子取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儿,得衣亦飞去。”
鬼车,一名鬼鸟,今犹九首,能入人屋收魂气,为犬所噬一首,常下血,滴人家则凶。《荆楚岁时记》:夜闻之,捩狗耳。言其畏狗也。白泽图云:“昔孔子、子夏所见,故歌之。其图九首,今呼为九头鸟也。”《毛诗义疏》曰:“鸮大如鸠,恶声,鸟入人家凶。其肉甚美可为炙。汉供御物各随其时,唯鸮冬夏施之以美也。”《礼‧内则》曰:“鸮胖。”《庄子》云:“见弹求鸮炙。”陈藏器又云:古人重其炙,尚肥美也。又按《说文》曰:“枭不孝,鸟至日捕枭磔之。”如淳曰:“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羹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愚谓古人尚鸮炙,是意欲灭其族。非为其美也。又《淮南万毕术》:甑瓦止枭鸣,取破甑向枭抵之,辄自止也。
7.《岭表录异》卷中(唐·刘恂著,约888年左右),取四库全书本
鸺鹠即鸱也,为囮,可以聚诸鸟。鸺鹠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虻。鸺鹠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行游女,与婴儿作祟,故婴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又曰:鸮大如鸩,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鸮炙。又云,古人重鸮炙,尚肥美也。说文:枭不孝鸟,食母而后能飞。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枭羮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鸮炙及枭羮,盖欲灭其族类也。
8.《太平广记》(宋·李昉等人编,978年),取四库全书本
鸱
鸱,相传鹘生三子,一为鸱。肃宗张皇后专权,每进酒,常以鸱脑和酒,令人久醉健忘。(出《酉阳杂俎》)
又
世俗相传,鸱不饮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饮。(并出《酉阳杂俎》)
鸺鹠目夜明
鸺鹠即鸱也,为囮,可以聚诸鸟。鸺鹠昼日,目无所见。夜则飞撮蚊虻。鸺鹠乃鬼车之属,也皆夜飞昼藏。或好食人爪甲,则知吉凶,凶者辄鸣于屋上,其将有咎耳。故人除指甲,埋之户内,盖忌此也。亦名夜行游女,与婴儿作祟,故婴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车,春夏之间,稍遇阴晦,则飞鸣而过,岭外尤多,爱入人家,烁人魂气。或云,九首,曾为犬啮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则有凶咎。荆楚岁时记云:闻之当唤犬耳。又曰:鸮大如鸩,恶声,飞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为炙,故庄子云:见弹思鸮炙。又云,古人重鸮炙,尚肥美也。说文:枭不孝鸟,食母而后能飞。汉书曰:五月五日作枭羮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以五日食之。古者重鸮炙及枭羮,盖欲灭其族类也。(出《岭表录异》)
又
或云,鸺鹠食人遗爪。非也,盖鸺鹠夜能拾蚤虱耳,爪蚤声相近,故误云也。(出《感应经》)
夜行游女
又云夜行游女,一曰天帝女,一名钓星。夜飞昼隐,如鬼神。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妇人。无子,喜取人子,胸前有乳。凡人饴小儿不可露处,小儿衣亦不可露晒。毛落衣中,当为鸟祟,或以血点其衣为志。或言产死者所化。(出《酉阳杂俎》)
9.《太平御览》(宋·李昉等人编,984年),取四库全书本
鬼車 《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多鬼車鳥,度家家槌門打戶,捩狗耳,滅燭燈禳之。《玄中記》云:此鳥明迕獲,一名天帝少女。夜游,好取人家女人養之,有小兒以血點其衣為驗。 《嶺表錄異》曰:有鳥如鵂留,又明屙車。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鑠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為犬齧下一首,常滴血。血滴之家,即有凶咎。 《三國典略》曰:齊後園有九頭鳥見,色赤似鴨,而九頭皆鳴。 《玄中記》曰:姑獲鳥,夜飛晝藏,蓋鬼神類。衣毛為鳥,脫毛為女人。名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游女,一名釣星,一名隱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人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荊州為多。昔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扶匐往,先得其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各走就毛衣,衣此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為婦,生三女。其母后使女問父取衣,在積稻下得之,衣之而飛去。後以衣迎三女,三女兒得衣飛去。(今謂之鬼車)
10.《猗觉寮杂记》卷下(宋·朱翌著,约1097~1167),取四库全书本
岭外人家,婴儿衣暮则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虫,名暗衣,见小儿衣必飞,毛著其上,儿必病寒,热久则瘦,不可疗。其形如大蝴蝶。又水经:豫章迳阳县多女鸟。元中记曰:新阳男子于水际得之,与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间养儿不露其衣,言是鸟落尘于儿衣中,令儿病。亦谓之夜飞游女。由此观之,乃暗衣也。
11.《本草纲目》(明·李时珍著,1578年),取四库全书本
姑获鸟(《拾遗》)
释名:乳母鸟(《玄中记》)、夜行游女(同)、天帝少女(同)、无辜鸟(同)、隐飞(《玄中记》)、鬼鸟(《拾遗》)、譩譆(杜预《左传》注)、钩星(《岁时记》)。时珍曰:昔人言此鸟产妇所化,阴慝为妖,故有诸名。
集解:藏器曰:姑获能收人魂魄。《玄中记》云:姑获鸟,鬼神类也。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云是产妇死后化作,故胸前有两乳,喜取人子养为己子。凡有小儿家,不可夜露衣物。此鸟夜飞,以血点之为志。儿辄病惊痫及疳疾,谓之无辜疳也。荆州多有之,亦谓之鬼鸟。《周礼》庭氏“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射夭鸟”,即此也。时珍曰:此鸟纯雌无雄,七八月夜飞,害人尤毒也。
后续的记载中姑获鸟的形象没有更多变化,不作摘录
如此罗列下来之后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姑获虽然发生过与鬼鸟、鸺鹠混同的记载,但就流传的内容本身而言并没有太多的变动。
那么在正式开始讨论姑获之前,首先让我们排除一切干扰因素,单纯地给姑获下一个定义。
姑获是什么?
是一种通过衣物对小孩作祟的妖鸟,穿上羽毛便能化作女子。
后文主要通过出处整理、要素猜测与原型追溯三个环节具体讨论姑获这一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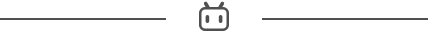
由于《玄中记》原书已佚,从《水经注》开始,依次序罗列姑获的内容。
《水经注》
郦道元以《水经》为纲,以河流为主要线索,记载了一千余条河流的地理形貌及相关的动植矿物、历史遗迹、人文传说等,具有极高的地理、文化研究价值。
就文本而言,《水经注》没有详细介绍姑获的意图,只是在描述富水流经阳新县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句而已。虽然没有指明姑获两字,不过就内容而言女鸟与后世所传姑获的内容十分相近,足以将两者视作同等。
内容包括:1.毛衣女故事。2.衣不夜露。3.以尘着衣取子。4.又名夜飞游女。
《荆楚岁时记》
首先,《荆楚岁时记》一书已经佚失。“正月夜,多鬼鸟度……”一句可以参考宋代的《太平御览》第十九卷与明代的《説郛》第六十九卷中的引用。才能所限,不讨论其中的真伪,姑且认为确有此句。
宗懔记载(杜公瞻作注)的荆楚地域年中每月行事的记录,是中国现有可考的最早系统性记载地区岁时民俗的专著。
就文本而言,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当中并没有直接出现姑获,出现的是“鬼鸟”。姑获具体出现在杜公瞻对“鬼鸟”的注解中。不论姑获是否等同于鬼鸟,杜公瞻的这份注解是姑获在现有可考的记载中第一次登场。
内容包括:1.名姑获,名天帝女,名隐飞鸟,名夜行游女。2.取人女子养之。3.以血点衣为志。4.荆州为多。
《本草拾遗》
陈藏器在《英公本草》的基础上编撰的一部药物学著作,虽然原书已佚,但依托于《证类本草》等书的收录与后人的辑佚,得以留存于世。姑获的段落就取自《证类本草》第十九卷中的收录 。
就文本而言,姑获列于禽部,前后两则分别为鸮目与鬼车(这三者在之后的记载中经常一起出现)。相对于杜公瞻在《荆楚岁时记》中的注解,这是姑获第一次正式出现在系统性整理的著作当中。
内容包括:1.收人魂魄。2.乳母鸟、产妇死变化作之。3.取人子以养之。4.胸前有两乳。5.名天帝少女、名隐飞、名夜行游女。6.以血点衣为志。7.衣不夜露。8.时人名鬼鸟。9.(引《荆楚岁时记》)名钩星、衣毛为鸟,脱毛为女。10.(引《左传》)鸟鸣于毫社。11.(引《周礼》)夭鸟。
《酉阳杂俎》
段成式所著的一部志怪小说,记载了诸多奇谈异闻。
就文本而言,《酉阳杂俎》中并没有直接记叙姑获,而是在第十六卷将夜行游女与其他鸟类的异闻并列记载。
内容包括:1.夜行游女、名天帝女、名钓星。2.夜飞昼隐如鬼神。3.衣毛为鸟、脱毛为女。4.无子,取人子。5.胸前有两乳。6.衣不夜露。7.毛落衣中则祟。8.以血点衣为志。9.产死者所化。
《北户录》
段公路所著的一部岭南风土录,以博物学的思路记叙了许多岭南地区独特的风俗传说,并引据了大量前人著述的内容。
就文本而言,《北户录》中的姑获出现在孔雀媒一篇中,大抵的思路是孔雀-媒鸟-鸱鸺-姑获-鬼鸟,就引注而言颇为详细,但有牵强附会之嫌。相对于杜公瞻的注解,这是姑获第一次“正式”与鬼鸟/鸱鸺/鸺鹠混同的记载。
内容包括:1.夜飞昼藏。2.名天帝少女、名夜行游女、名隐飞。3.取小儿食之。4.衣不夜露。5.以血点衣为志。6.衣毛为鸟、脱毛为女。7.豫章毛衣女故事。
《岭表录异》
刘恂以自身在广州的经历为基础所写的一部岭南风土录。原书已佚,此处的内容源自《太平广记》的引用。
就文本而言,《岭表录异》中的内容讲的主要是鸺鹠而不是姑获,可以视作混同现象的延续。
内容包括:1.名夜行游女。2.衣不夜露。
《太平广记》
李昉等人奉宋太宗的命令集体编纂的一部野史小说总集,以故事的内容作为细分的依据。赖于《太平广记》的收录,大量唐代(及之前)佚失的作品得以继续流传于世——譬如上面所引的《酉阳杂俎》与《岭表录异》,两者的辑佚都大量采用了《太平广记》的记载。
就文本而言,姑获并没有直接出现在《太平广记》的记载当中,而是以夜行游女的形式收录在【第四百六十二卷-禽鸟三-枭】一项里。大致的思路是枭(大项)-鸱-鸺鹠-夜行游女。此处以《岭表录异》为据,夜行游女与鸺鹠、鬼车混同在一起。
内容同上述《酉阳杂俎》与《岭表录异》
《太平御览》
李昉等人奉宋太宗的命令集体编纂的一部类书,其征引内容之广博,为宋四大书之最,统共一千卷,分五十五门,总括大小类目五千四百七十四类。
就文本而言,姑获出现在【第九百二十七卷-羽族部十四-异鸟-鬼车】一项里。大致的思路是鬼车(大项)-鬼车鸟-鸺鹠-九头鸟-姑获鸟。此处以《荆楚岁时记》为据,姑获鸟被冠以鬼车之名,与鸺鹠和九头鸟混同在一起。
内容包括:1.夜飞昼藏。2.鬼神类。3.衣毛为鸟,脱毛为女。4.名天帝少女、名夜行游女、名钓星、名隐飞鸟。5.无子,取人子养之。6.不露其衣,鸟度则取小儿。7.荆州为多。8.毛衣女故事。
《猗觉寮杂记》
朱翌所撰的杂记,上卷考据诗词歌句,下卷杂议风俗史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引据精凿,在宋人说部中不失为《容斋随笔》之亚。
就文本而言,《猗觉寮杂记》中并没有直接记叙姑获。这段内容主要是讲岭外人家衣不夜露的习俗,作为参考引用了《水经注》和《玄中记》中的内容。
内容同上述《水经注》
《本草纲目》
李时珍所撰的药物学、博物学著作,共五十二卷,分作十六部六十类目,总括药物1892种、方剂11096首。得益于明朝相对活跃的文化交流,《本草纲目》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1607年,《本草纲目》传播到了日本,引起了德川家康的注意。1612年,林罗山对《本草纲目》中记叙的种种条目以日语的训读标上和名,并在此基础上增添了一些个人的看法,编撰出了《多识编》,其中就包括姑获鸟。
就文本而言,姑获鸟收录于【第四十九卷-禽之四-山禽类-姑获鸟】一项里,主要引用了《本草拾遗》的内容,并增添了李时珍个人的见解。
内容包括:1.名乳母鸟、名夜行游女、名天帝少女、名无辜鸟、名隐飞、名鬼鸟、名噫嘻、名钩星。2.能收人魂魄。3.鬼神类。4.衣毛为鸟,脱毛为女。5.产妇死后化作,胸有两乳。6.取人子养为己子。7.衣不夜露。8.以血点衣为志。9.儿病之得无辜疳。10.荆州多有之。11.夭鸟。12.纯雌无雄。13.七八月夜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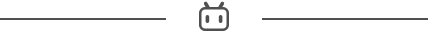
在逐条分析姑获包含的要素之前,首先将上述内容的条目以出现次数的多寡为顺序依次排列
名夜行游女,名天帝女,名隐飞。又名鬼鸟,名噫嘻,名钩星,名乳母鸟。
以血点衣为志,故养儿衣不夜露
取人子养之
衣毛为鸟,脱毛为女
夜飞昼藏
产死者所化,胸前有两乳
豫章男子与共居,生女衣羽而去
荆州为多
鬼神之属,能收人魂魄
为了方便理解,更进一步地将条目划作四种
A·名字-1
B·习俗(衣不夜露)-2
C·传说(毛衣女故事)-3、4、7
D·衍生(后人增述)-5、6、8、9
A·夜行遊女、夜飞遊女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在晚上出行的女子,凸显的是姑获身上夜行性与女性的属性。结合内容看来,夜行遊女的名字是源自姑获鸟在夜间作祟的习性。《水经注》与《猗觉寮杂记》中作夜飞遊女,额外凸显了飞行的属性。※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废除了遊的写法,但在古代遊与游是两个字,比如《说文解字》里就有游与遊两种不同的写法,遊比较适用于陆地上的活动,游则适用于与水相关的活动,不过通常两者并没有十分严格的划分。归到游女与遊女的说法,遊女指的是出遊的女子,而游女则有汉水女神的含义,在这里个人认为夜行遊女与汉水女神并无关联。关于汉水女神的研究可以参考梁中校的《汉水女神考论》 一篇。
A·天帝女、天帝少女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天帝的女儿。这一项在姑获的形象中可以说是十分突兀,很难看出与内容的关联。但联系到《玄中记》的作者郭璞,天帝女就有另一层不同的含义了。
参考郭璞所注《山海经》卷五-洞庭之山一节(取四库全书本):
……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
今长沙巴陵县。西又有洞庭陂,潜伏通江。 《离骚》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叶。下皆谓此也。字或作铜,宜从水。
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麋芜、芍药、芎藭。
麋芜,似蛇牀而香也。
帝之二女居之,
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即《列仙传》江妃二女也。《离骚·九歌》所谓湘夫人,称帝子者是也。而《河图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尧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风,而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闻之尧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传》曰:二女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为湘君。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尧女?且既谓之尧女,安得复总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礼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义可知矣。即令从之,二女灵达,鉴通无方,尚能以鸟工龙裳,救井廪之难,岂当不能自免于风波,而有双沦之患乎?假复如此。《传》曰:生为上公,死为贵神。《礼》:五岳比三公,四渎比诸侯。今湘川不及四渎,无秩于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灵神祇,无缘当复,下降小水,而为夫人也。参考其义,义既混错,错综其理,理无可据,斯不然矣。原其致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为名,名实相乱,莫矫其失,习非胜是,终古不悟。可悲矣。
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
此言二女游戏江之渊府,则能鼓三江,令风波之气共相交通,言其灵响之意也。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子》曰:弋钓潇湘今所在。未详也,潇音萧。
是在九江之间。
《地理志》:九江,今在浔阳南江。自浔阳而分为九,皆东会于大江。《书》曰:九江,孔殷是也。
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可以看到在“帝之二女居之”一句的注解中,郭璞引用了大量文献,着重讨论了湘夫人和尧女两者由于“帝女”一名产生的同形异义问题,认为这种混淆的现象“名实相乱”,“习非胜是”。此处不讨论湘夫人和尧女的形象流变过程,重点在于“帝女”一词的混淆现象本身。
以个人的观点看来,“天帝少女”或“天帝女”一名,是郭璞以姑获身上包含的怪鸟这一身份作为切入点,出于刻意混淆的目的赋予姑获的异名,实质上并不是说姑获真的有这么一层带有神性的身份。
A·隐飞、隐飞鸟
隐飞这个词无从考据,姑且拆开来理解成隐(形容词)飞(动词)。“隐”字一般用作动词,很少用来形容另一个动词。按郭璞《尔雅注疏》所述:
瘗、幽、隐、匿、蔽、窜,微也。 释曰:微谓逃藏也。瘗者,埋藏之微也。幽者,深微也。隐者,潜隐而微也。匿者,舍人曰:「藏之微也。」蔽者,覆障使微也。窜者,行之微也。是皆微昧不显扬也。 可以看出,隐作形容词时有潜藏的意思。按字面理解,“隐飞”就是潜隐飞行的意思,强调的是姑获行踪诡秘的属性。
A·鬼鸟、鬼车鸟
鬼鸟一般认为是九头鸟,将姑获认作鬼鸟源自《荆楚岁时记》的误传,并在唐宋的博物学中广泛传播。但实际上姑获鸟并不是鬼鸟,这点在《本草拾遗》中也有记载。
鬼車,晦暝則飛鳴。能入人室,收人䰟氣。一名鬼鳥。此鳥昔有十首,一首為大所噬,今猶餘九首,其一常下血,滴人家則㐫。夜聞其飛鳴,則捩狗耳,猶言其畏狗也。亦名九頭鳥。《荆楚歳時記》云:姑獲,夜鳴聞則捩耳。乃非姑獲也,鬼車鳥耳,二鳥相似,故有此同。《白澤圖》云蒼鶊,昔孔子與子夏所見,故歌之,其圖九首。
A·噫嘻、嘻嘻、譆譆
鸟叫声,与姑获的关联尚不明晰。按《本草拾遗》述,典出《左传》
(襄公三十年) 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或呌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A·钩星、钓星 星名,参考《晋书》与《星经》
大致的意思就是造父星西边有九颗排着像钩子的星星,这九颗星星排列变直的时候就会发生地震。算是中国浩如烟海般的星辰传说中的一则,与姑获的关联尚不明晰。
A·乳母鸟
名出《本草拾遗》与《本草纲目》,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哺育人类孩子的鸟。按《本草拾遗》所述,乳母鸟是后人附加的名字。附加的根据大抵是姑获偷小孩当做养女的习性,既然要偷去当养子,就肯定要哺育偷来的孩子,于是产生了乳母鸟的说法。
B·以血点衣为志,故养儿衣不夜露
这句可以分成两个部分,首先是豫章地区衣不夜露的习俗,其次是姑获以血点衣的习性。
关于衣不夜露的习俗,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习俗产生的地点与作用的人物。首先按《水经注》与《猗觉寮杂记》的记载,这个习俗流传的地点在南方地区(豫章/岭南)而不是北方,个人猜测可能的原因是南方地区气候潮湿(按《汉书·地理志》“江南卑湿,丈夫多夭”),晚上晒衣服可能晒不干,又或者会沾到露水。另一个要素是小儿,由于小孩免疫力较弱,穿上没有晒干的衣服更容易得病导致早夭。实际上仅就晚上不晒衣服这一点来说,现代依旧流传着不少相关的迷信故事。
关于以血点衣的习性,在《水经注》里说是鸟落尘于儿衣中。个人的猜想是当时的南方地区还不够发达,鸟类与人类的主要活动地点重合,某种夜鸟在晚上活动时会在晒的衣服上留下尘土或排泄物,导致衣服沾染细菌,而细菌又会对免疫力低的儿童造成影响,因此产生了姑获“以血点衣为志”的说法。说到夜鸟自然会联想到猫头鹰,郭璞的《尔雅注疏》中也有相关的记载
[疏]「萑,老鵵」 释曰:老鵵,一名萑。 郭云:「木兔也。似鸱鸺而小,兔头,有角,毛脚。夜飞,好食鸡。」
可惜仅凭这点无法判断姑获等于猫头鹰。总体看来这部分的内容应该也是先果后因的一种传说。显然并不是真的有一种叫姑获的鸟会用血点到衣服上来偷小孩,而是因为有人家养小孩的时候在晚上把小孩的衣服晒到外面,衣服上沾染了脏污,之后穿着衣服的小孩死了,于是产生了养儿衣不夜露的习俗与一种以血点衣取小儿的怪鸟。
C·取人子养之/食之
按字面理解就是把人类的孩子偷过来自己养,也就是以血点衣取小儿的后续情节。“养”这个动作非常微妙,遭到作祟的小儿并不是死了,而是被姑获鸟偷走当成了养子。按个人的观点,很难想象一种民间流传的传说会这么“温柔”,应该是姑获这个形象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设计的。养小儿的动作可能是源自《搜神记》中毛衣女与男子生三女、迎三女的情节,故事中的毛衣女迎走女儿可以视作“取人子”,而由于毛衣女母亲的身份又可以判定取子后会“养之”,总体来说是郭璞将民间习俗与故事进行的主动结合。关于姑获与《搜神记》的关系到溯源部分再加详述。
C·衣毛为鸟,脱毛为女
取自《搜神记》
C·豫章男子与共居,生女衣羽而去。
取自《搜神记》
D·夜飞昼藏
顾名思义,晚上行动,白天隐藏,根据大抵是衣不夜露的习俗,强调的是姑获的夜行性。
D·产死者所化,胸前有两乳。
源自《本草拾遗》,个人猜测是对姑获“取人子养之”这一行为赋予的动机与属性。既然姑获会偷小孩自己养,那么姑获肯定能够为小孩哺乳,于是“胸前有两乳”。因为姑获是由“产死者所化”的,于是便偷人家的小孩当做养子。
D·荆州为多
姑获在荆州为多这点出自《荆楚岁时记》,内容中所引用的事例地点却是扬州豫章,虽然荆杨两地相近,不过参考到《搜神记》毛衣女故事里的新喻一地,这里又有另一种说法。
依《太平寰宇记》记载,汉时,新喻本为宜春县之地,属豫章郡。东吴宝鼎二年十二月,末帝孙皓分宜春,采渝水为名,立新喻县。划豫章郡、庐陵郡、长沙郡,又立安城郡。安成郡统平都、宜春、新喻、永新、安复、萍乡、广新七县,隶扬州。太康元年,晋武帝灭吴,扬州安成郡改隶荆州。所以按两晋的划分算来,新喻居于荆州安成郡的下辖。
D·鬼神之属,能收人魂魄
出自《本草拾遗》,显然姑获并不是实际存在的鸟类,因此陈藏器将其划作了鬼神之属,并赋予了收人魂魄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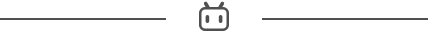
相较于上面的出处整理与要素猜测,接下来的部分将以个人创造为主。
关于流传下来的姑获鸟的内容,除去名字与后人的增述,可以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衣不夜露、以血点衣,另一部分是衣毛为鸟,脱毛为女。前一部分的传说没有可考的出处,后一部分则是出自《搜神记》。为了考察姑获鸟的形象,首先对毛衣女故事进行粗略的剖析。
郭璞与干宝
晋元帝时,郭璞和干宝两人同朝为官,曾一同共事麟台。东晋初期朝内未置史官,干宝经中书监王导举荐任为著作郎,领修东晋国史。其人性好阴阳术数,通晓易学,与葛洪、韩友等人交好。 郭璞以《南郊赋》一文被晋元帝提为著作佐郎,后迁为尚书郎。其人博学高才,好古文奇字,妙于阴阳算历,精通五行、天文、卜筮之术,然而性格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与温峤、庾亮等人交好。干宝曾批评过郭璞的生活作风问题,言其“此非适性之道也”。 《搜神记》中记有七则郭璞的故事,其中就有郭璞撒豆成兵为“红颜”的轶事。虽然两人称不上莫逆之交,但还是有一个共同的喜好,那就是阴阳术数。《太平御览》方术部中提到干宝为神女智琼占算,并请郭璞为之作解。 故事的真实性姑且不论,总之个人猜测郭璞与干宝既是同事,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两人或许私下会聊聊神鬼之事,郭璞从干宝所述的毛衣女的故事中得到灵感,创作出了姑获这一形象。
《毛衣女》
依《搜神记》序言,其中故事大致分作两类,一类是整理先人故籍的传说,一类是行访事于故老的逸闻。在现存书籍的范围内,毛衣女的故事此前并无记载,无从查证毛衣女在晋朝以前的流传,姑且作为民间口传故事来考虑,由于《搜神记》中没有描述具体的时间背景,尝试从故事中的地点切入。
《搜神记》以豫章新喻称之,可以有两种思路:其一以豫章为重,毛衣女可能是在新喻一地自汉代(或更早)开始一直流传至东晋的故事;其二以新喻为重,新喻县于东吴宝鼎二年初创,毛衣女可能是从两晋(或东晋)方才产生的新的传说。同上所述,由于无从查证晋朝以前的流传,此处仅考量第二种说法,即毛衣女是一种新的传说故事。接下来聊一聊毛衣女故事的内容:
见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鸟。田中:故事的地点。推测为民间传说。六七女:女子的人数众多。推测女子一方形成聚居,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毛衣:参考《搜神记》雌鸡化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的故事 ,可以认为当时的毛衣指的就是禽类的羽毛。推测毛衣的说法是一种对女子方的歧视。
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匍匐:特地指明匍匐的动作,推测田地中的作物已经生长到了一定高度,但还没有收割。推测故事发生时间为夏秋之间。
诸鸟各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取以为妇:《搜神记》中人类男子与神/怪女子结婚的故事并不多见,除了毛衣女故事之外还可以论的上是结婚的故事另有四则:董永与天之织女的故事、弦超与玉女智琼的故事、秦闵王之女的故事、谈生与睢阳王家之女的故事。这四则故事与毛衣女故事有两个很明显的不同之处:1.发生的地点。2.女方的意愿。四则故事中,前两则的女性主角都是天女,结婚由女方提出,更类似于公事公办,并没有夫妻之实;后两则的女性主角都是死者,结婚姑且可以算做“两情相悦”,结果都是男方主角变成了女婿,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在毛衣女故事中,即使称作“结婚”都有些勉强,倒不如说是男子强迫女子为妇,由此推测双方的关系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知衣在积稻下:衣在积稻下女子却不知,可以推测女子没有从事农务,或许是在从事纺织
后复以迎三女,女亦得飞去。女子特地回家来迎走孩子,可以视作女子对男子的报复,或者资源的回收。
通过文本我们可以大致概括出两个角度的故事:男子方面:遇女,得衣,藏衣,取女为妇,得子,失子女子方面:暴露,失衣,被取为妇,生子,得衣,逃走,迎女
社会背景
既是民间传说,就不得不提到两晋时的人民迁徙活动了,此处引用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中的段落:
(第三章-第三节)西北各族入居中原内地之后,因受西晋地方官吏和汉族地主的剥削与压迫,不断起来反抗。如在西晋泰始中,鲜卑秃发树机能举兵凉州,历十年之久。惠帝元康四年,匈奴族人郝散起兵上党谷远,元康六年,氐帅齐万年起兵关中,郝散弟郝度元联结冯翊、北地羌、胡族人举兵相应。秦、雍二州氐羌族人也奋起参加,有众数十万,声势浩大,连败政府军。他们都先后失败。可是秦雍一带,自惠帝永熙元年起,由于水利失修,无年不旱。到了元康四年,便造成了严重的饥馑。元康七年以后,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饥荒更是严重,“米斛万钱”,正是“疾疫荐臻,戎晋并困”此后“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在大旱荒大饥饿的情况下,秦、雍等州各族人民不得不流徙至梁、益、荆、豫等州就食。冀州的汉族人民,也在饥旱与日益壮大的匈奴贵族势力威胁之下,不得不流徙至冀、豫等州就食。冀州的汉族人民又不得不流徙至兖州一带就食。
秦雍流民流徙至梁、益之后,西晋在益州的统治即告结束,益州的汉族农民,流徙到荆、湘地区,或南入宁州的很多。宁州连年饥疫,人民死亡在十万人以上,西晋在宁州的统治也濒于瓦解的前夜,在宁州的吏民,又有不少人由宁州撤退至交州一带。
当李特、李流领导流民和西晋益州官吏进行斗争之际,巴蜀的土著居民数万家流亡到荆湘地区。他们到达荆、湘以后,由于受到荆、湘二州官吏、地主的歧视和压迫,起义的事件也是不断的发生。蜀人李驤在乐乡领导流民起义,杀死县令。西晋荆州刺史王澄派兵袭杀李驤,并沉杀巴蜀流民八千余人于长江。流民更为怨忿,蜀人杜畴再次聚众起义。湘州刺史荀眺也认为“巴蜀流民皆欲反”,“欲尽诛流民。流民大惧,四五万家一时俱反。”,并推“以才学著称”,有“州里重望”的益州秀才杜弢为首领。公元311年,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起义军攻下长沙,生擒荀眺,复南破零陵、桂阳,东袭沔阳、豫章,杀了不少西晋的贪官污吏。公元315年,晋琅琊王司马睿命王敦、陶侃集结大军,围攻杜弢,前后数十战,弢兵力损折甚多,部将王贡投降官军,弢突围出走,中途病死,这次坚持四年的流民起义也就失败了
…… (第五章-第二节)中原人民流亡南下,除了巴蜀流民在永嘉之前已布满荆湘一带外,此外可以分作七个时期。
永嘉元年(307),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这是第一个时期
太兴四年(321),祖逖病死,郗鉴自鄒山退屯赫妃,祖约自谯城退屯寿春,其后遂尽失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流民渡江者转多,这是第二个时期
永和五年(349),梁犊起义雍城,石虎愁怖病死,石赵政权崩溃,桓温出兵关中,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
太元八年(383),淝水大捷,茯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流民相率渡江,这是第四个时期。
……
可以看到,一方面,由于起义、水利失修、旱灾、蝗灾、疫病等多方面的影响,北方土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南下谋生。另一方面,对于南方土民而言,北方流民的涌入有损无益,不仅有排外心理的影响,大量的外来人口势必会侵占本地的资源。对于南方的既得利益者(官吏与地主)而言也是如此,流民无法上税,一时间也无法当做稳定劳动力使用。在双方的歧视与压迫下,流民与土民的矛盾之激烈亦是不难想象。在这个流民矛盾日益激化的背景下,东晋成立了。晋元帝为了稳定局势,防止南方再发生流民起义,设立了桥州郡与土断的制度,一方面将流民收容到侨州郡中减少土民与流民的矛盾,一方面通过整理户籍保证了流民的权益(对流民的管制)
假说
排除超现实的要素,整体而言毛衣女故事所展现的是流民和土民之间的冲突。故事中的男子属于荆湘本地住民,而女子属于外地流民。西晋时由于社会动荡南下的流民既没有政府保障的权利,又没有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只能被动地依附于权贵与地主阶级,流民不堪忍受本地人的歧视与压迫,发起了起义,但由于势单力薄,流民起义皆以失败告终。东晋政权建立后,为了防止流民再次起义,晋元帝对流民的权利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维持了南方地区的相对稳定态势。
即使如此,土民和流民之间的歧视与对抗也不会陡然消失,而是进入一种相对缓和的对立状态,而在这种状态中诞生的就是毛衣女的故事。男子取女子为妇后生女代表了双方关系的相对缓和,男子窃衣与女子携子逃跑代表了双方关系中存在的无法调和的矛盾。
姑获
在解释一切的关系之前,首先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摆在眼前——
姑获为什么叫姑获?
“姑”,姑且当做是妇女的意思。那么“获”是什么呢?
按杨雄所撰、郭璞加注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所述:
臧甬、
音勇
侮获,奴婢贱称也。 荆淮海岱杂齐之闲,
俗、不纯为杂。
骂奴曰臧,骂婢曰获。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皆异方骂奴婢之丑称也。自关而东,陈魏宋楚之闲、
保庸谓之甬。 保言可保信也。
秦晋之闲,骂奴婢曰侮。
皆为人所轻弄。 案《后汉书·何敝传》:然臧获之谋。注引《方言》:臧获,奴婢贱称也。 《荀子·王霸篇》:则虽臧获。杨倞注云:臧获,奴婢也。《方言》谓荆淮海岱之闲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齐亡奴谓之臧,亡婢谓之获。或曰取货谓之臧,擒得谓之获。皆谓有罪为奴婢者。故《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槀。
《史记·鲁仲连列传》:臧获且羞与之同名矣。裴駰集解引《方言》:荆淮海岱燕齐之闲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齐即杂齐之讹。《广韵》引《方言》作荆淮海岱淮济之闲,杂齐、淮济字形相近而讹,各本壻讹作聓。
《汉书·司马迁传》: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注引应劭曰:扬雄《方言》云:海岱之闲,骂奴曰臧,骂婢曰获。燕之北郊,民而聓婢谓之臧,女而妇奴谓之获。聓字亦转写之讹,徐坚《初学记》引《方言》此条作壻,今据以订正。
《司马相如列传》:与保庸杂作。集解引《方言》:保庸调之南方奴婢贱称也。调乃谓字讹舛,南方二字乃甬字讹舛,甬作勇,遂离而为南方,亦校书者妄以意改也。
贾谊《过秦论》:材能不及中庸。李善注引《方言》:庸,贱称也。
《广雅》:甬,保庸使也。侮,获婢也。
所谓的姑获就是对女性奴隶的一种污蔑性的称呼,这点继承自《搜神记》毛衣女的故事,根源是南方土民对南下流民的歧视。
最后,让我们将毛衣女与习俗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毛衣女与习俗有两个最大的“共同点”。
毛衣女可以衣毛为鸟,而习俗中作祟的正体就是一种怪鸟。
毛衣女的结局是毛衣女带走了自己生的孩子,对于男方而言无疑是“夺子”的行为,而习俗中的鸟会使孩子生病,使孩子生病死亡也可以视作一种“夺子”的行为。
以我看来,郭璞将两个传说故事互相结合,根据习俗创造了夜行游女与隐飞的名字,根据怪鸟创造了天帝少女的名字,根据毛衣女创造了姑获的名字,最后诞生了姑获这种衣毛为鸟,脱毛为女,好取人子养之,以血点衣为志的怪鸟。
【相关文章】
本文地址:http://www.yesbaike.com/view/144404.html
声明:本文信息为网友自行发布旨在分享与大家阅读学习,文中的观点和立场与本站无关,如对文中内容有异议请联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