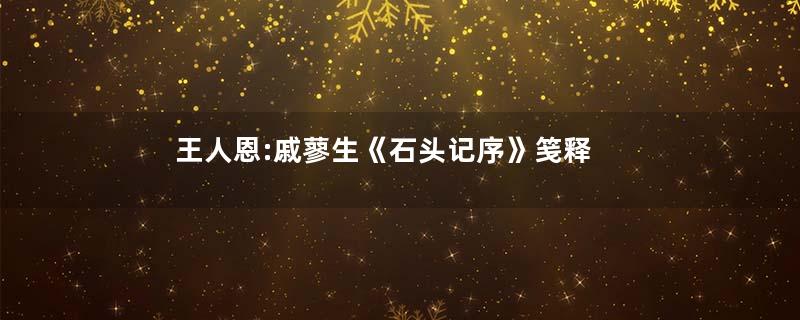
(文章刪改自王人恩《红楼梦考论》十一 戚蓼生《石头记序》笺释。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从红学史来看,德清戚蓼生(?—1792)的《石头记序》虽然仅有四百六十七个字,但由于见解新颖、内涵丰富、用典精辟而一直为红学研究者所珍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认为这篇序文“笔调非凡,见地超卓,已足名世不朽”;多年来致力于戚蓼生研究的著名红学家邓庆佑先生于1996年指出:戚蓼生“对《红楼梦》的研究和理解,是何等深刻!他是一个真正读懂了《红楼梦》,而且千百年后,人们也会承认他是红学史上一个有突出贡献的人”;近来他又进一步论道:“戚蓼生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伟大的红学家,他的序言如果后人不给加上标点,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百六十七个字,但对《红楼梦》艺术成就的阐释,甚至比后世一些红学家十百万言的《红楼梦》艺术专著,把握得还要准确,论述得还要深刻。”若对戚蓼生序文深入研读,即可感知周、邓所言绝非拔高过誉之词。遗憾的是,这篇重要的红学研究资料迄今尚无人作过笺释,其中的新颖见解、典故隶用给阅读者留下了拦路之虎。因此导致“这篇出色的也是最早的红学评论文章,从来不受重视,从清代到民国,极少为人提起,实为怪事”。笔者不揣浅陋,拟仿陈子谦先生《〈谈艺录•序言〉笺释》一文作一笺释。
原序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一]。神乎技矣[二]!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三],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四]。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五],目送而手挥[六],似谲而正,似则而淫[七],如《春秋》之有微词[八],史家之多曲笔[九]。试一一读而绎之[十]: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十一];状阀阅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十二];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十三];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十四]。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芗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十五]。盖声止一声,手止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十六]。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十七]?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十八]。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有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十九]。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二十]。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二十一]?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二十二],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二十三]。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万千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二十四]。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二十五]!德清戚蓼生晓堂氏[二十六]。
笺释
[一]绛树两歌、黄华二牍:绛树,古歌女名。据《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乐部”三“歌”引曹丕《答繁钦书》“今之妙舞莫巧于绛树,清歌莫善于宋腊”之“今”而言,绛树似为东汉、三国初人。又“绛树”与“宋腊”相对为文,可知绛树非艺名或小名,或姓“绛”名“树”。考“绛”本为地名,在今山西翼城县西南,晋穆公自曲沃迁都于绛,后以邑为氏。然典籍中姓绛者几希,“绛树”其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南朝梁庾肩吾《咏美人》:“绛树与西施,俱是好容仪。”是知至南北朝时,绛树以貌美传世,而南朝徐陵《杂曲》云:“碧玉宫伎自翩妍,绛树新声最可怜。”仍把绛树比作善歌者。至唐冯贽《记事珠》始对绛树的歌技有了开拓性的描述:“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二人相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人疑是一声在鼻。”然仅言一声能歌两曲,“一声在鼻”已含“一声在喉”之义。对绛树进行夸张描述者当推元人伊世珍《嫏嬛记》:“绛树一声能歌两曲,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人疑其一声在鼻,竟不测其何术。当时有黄华者,双手能写二牍,或楷或草,挥毫不辍,各自有意。余谓‘绛树两歌’、‘黄华二牍’,是确对也。”两相对照,“绛树两歌”之事,《嫏嬛记》似从《记事珠》而来,而“黄华二牍”一事则系《嫏嬛记》所独言。又从“当时”二字来看,黄华亦为人名,与绛树是同一时代人,至于是男是女,则不得而知。与曹雪芹同时代人翟灏《上元日琉璃厂观百戏作俳体五十韵示同游诸子》就有“黄华双牍并,绛树两歌歧”诗句,并自注“绛树能一声歌两曲,黄华双管并下,见《嫏嬛记》”。戚序用此二典旨在铺垫下文他对《红楼梦》艺术特色和艺术成就的赞赏。
[二]神乎技矣:是对绛树、黄华高超技艺的赞美,谓语“神乎”提前是强调其“神”。赞美绛树、黄华之技艺高超同样是为下文赞美《红楼梦》作铺垫。
[三]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由前诸层铺垫跌出写作序文的主旨:世间万万不能有的奇事竟然在《石头记》书上发生了,作者是用惊叹无已的口吻认定《石头记》乃“千古未有之奇书”,从而对《石头记》的赞誉推至旷古未有、无以复加的地步。要义有二:绛树固然歌技高明,能一声两歌,但不过一声在喉,一声在鼻,可谓人籁而非天籁,故听者“细”听尚能辨之;黄华固然书法高妙,能一手二牍(今在电视上亦能见到),但不过左腕书楷,右腕书草,亦可谓人工而非天工,故后天经过学习可臻此境。总之,绛树、黄华之技人间可闻,世间可见。此其一。而《石头记》既能一声两歌,一手两牍,有绛树、黄华人籁人工之技,又能“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无区乎左右”,超迈前人而直臻妙手天成之境,绝非绛树、黄华之技可比。故云“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质言之,《石头记》成功的原因在于作者能够继承以前一切优秀文化的优秀传统而又
能创造出全新的作品的意思在内。这是非常值得珍视的见解。姑举二例以明之:第一,《红楼梦》深受楚辞文化的巨大影响而能推陈出新,屈子的人格、屈赋奇幻的风格、讽兼比兴的象征艺术、《芙蓉女儿诔》的创意和表现手法、环境描写、湘云的命运、黛玉的题帕诗等方面,都明显地表明了曹雪芹对楚辞的继承和创新,请参阅拙文《〈离骚〉未尽灵均恨更有情痴抱恨长——试论〈红楼梦〉与屈原赋》。第二,发生于西汉、定型于晋代的王昭君故事也大大影响了《红楼梦》的创作,曹雪芹似有“昭君情结”,小说中歌咏昭君的诗歌多所创新,它还借昭君比黛玉,借昭君和番影射探春远嫁,从而大大升华了昭君故事的内涵,增强了《红楼梦》的艺术魅力,请参阅拙文《〈红楼梦〉与昭君故事》。
[四]夫敷华掞藻……姑不具论:敷华,铺陈文采。敷,铺陈。谢灵运《山居赋》:“敷文奏怀。”《文心雕龙•镕裁》:“引而伸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华,文采。三国魏钟会《孔雀赋》:“五色点注,华羽参差。”掞藻,铺张辞藻,与“敷华”义近,谓施展文才。萧颖士《赠韦司业书》:“今朝野之际,文场至广,掞藻飞声,森然林植。”立意,指作者写作《石头记》的用意,即所谓创作动机和目的。遣词,即用语。立意遣词盖指内容形式两方面而言。窠臼,现成格式,如窠巢、舂臼,喻指蹈袭故常,不能自出心裁。朱熹《答许顺之书》:“此正是顺之从来一个窠臼,何故至今出脱不得?”“无一落前人窠臼”正从脂批而来:“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窠臼”,又直启鲁迅名言:“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五]第观其……注此而写彼:第,转折连词,但。蕴于心而抒于手,盖指作者构思和写作的过程而言,“蕴于心”亦即胸有成竹,“抒于手”亦即走笔书写。注彼而写此:周汝昌先生说:“注此写彼,有无出典?我愧未详。这大约有点儿像武术上的‘指东打西’,战略上的‘声东击西’,或者有似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谋略。用‘大白话’说,就是:你读这些字句,以为他就是为了写‘这个’,实则他的目标另有所在,是为了写‘那个’!”我以为,“注彼而写此”似从晋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序》及孔颖达疏变化而来:“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孔颖达疏云:“文见于此,谓彼注云辞微而义显也。”接下具体论析成公十四年、僖公十四年和十九年所叙之事,三次重言“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准此,则“注彼而写此”之要义是“辞微而义显”,它是后人对《春秋》记事特点的艺术概括。考杜预之《序》所谓“五例”实从《左传》成公十四年九月而来:“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孰能修之!’”又《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冬亦载:“《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辩。”联系戚序下文“如《春秋》之有微辞,史家之有曲笔”来看,“注彼而写此”的核心内涵是指《石头记》与《春秋》有近似之处:辞微而义显,即文辞背后含有隐晦的批评,但它的义旨显明,读者可以领悟。这实际上已经认识到了小说与史书的相同的社会功能和相似的写作手法问题,可以看作戚蓼生对红学的重要贡献之一,因为它是红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史传对小说具有深刻影响的高明见解,对后来的研究者影响甚大。如刘铨福就有“《红楼梦》虽小说,然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的评论。《红楼梦》之有“微言大义”是客观存在,历久不衰的索隐派红学所提出的种种奇谈怪论恰恰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一点。大量的脂批文字透露出,《红楼梦》采用的手法是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小说的本旨是“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此书不敢干涉朝廷”,然而它又不时提醒读者要注意小说背后的“隐寓”,姑举三例:第一回有“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失落无考”一句,甲戌本有侧批云:“若用此套者,胸中必无好文字,手中断无新笔墨。据余说却大有考证。”第五回写宝玉听了十二支曲的几支曲后,“也不察其原委,问其来历,就暂以此释闷而已”,甲戌本有眉批云:“妙。设言世人亦应如此法看此红楼梦一书,更不必追究其隐寓。”第十六回写赵嬷嬷与琏、凤谈及元春省亲一事,甲戌本有回前总批云:“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惜(昔)感今。”凡此均说明《红楼梦》的确有“微言大义”,不过写得隐晦一些罢了,作者的爱憎态度隐藏得隐蔽一些罢了,而读者须细心领会,正如脂评所提示“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敝(蔽)了去,方是巨眼”。
[六]目送而手挥:语出嵇康《赠秀才入军》诗之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诗写嵇康之兄嵇喜在行军途中领略大自然情趣的自得之情,眼望远去的归鸿,手弹怀中的琴弦,自由自在,忘怀陶醉。戚文借以比喻作者写《石头记》能做到手眼并用,挥洒自如。周汝昌先生指出:“目送手挥,倒是有典可查的:晋代的阮籍,最善操琴(七弦古琴),记载说他弹奏时是‘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手倒是在弦上,眼却一意地随着遥空的飞雁而远达天边了!这说的是手之与目,音之与意,迹之与心,是活泼泼而神通而气连的,然而又不是拘拘于一个死的形迹之间的。……换言之,就是‘一笔二用’的意思。”恐是误记,不过其解说倒是有一定参考价值。
[七]似谲而正,似则而淫:似谲而正,语出《论语•宪问》:“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戚氏借孔子评论人物之言评论《石头记》的风格看似谲怪奇异而实际上端正严肃。似则而淫,看似有法则而又有些过度。则,法则。《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淫,过度。《左传•襄二十九年》:“迁而不淫,复而不厌。”戚氏此二句实从《论语•八佾》孔子所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二句模仿而来。
[八]如《春秋》之有微词:《春秋》,相传为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的编年体史书。《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因史记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何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又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序》认为“以一字为褒贬”,《汉书•艺文志》认为含有“微言大义”。故后来就把文笔深曲、意含褒贬的文字称为“春秋笔法”。戚蓼生敏锐地读出了《石头记》的“春秋笔法”,向读者指明了阅读《石头记》的不二法门,令人钦敬。脂批也多处指出《石头记》的“春秋字法”、“《春秋》的法子”,如第三回写贾雨村带林黛玉进京后,拿着林如海的书信拜见贾政,贾政竭力协助,就帮贾雨村“轻轻谋取了一个复职候缺”,甲戌本有夹批:“春秋字法”。接下又在“不上两个月,金陵应天府缺出,便谋补了此缺”旁复批有“春秋字法”。其实,此前写“雨村相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这贾政最喜读书人”一节文字旁的夹批,也正是“春秋字法”:“君子可欺以其方也。雨村当王莽谦恭下士之时,虽政老亦为所惑,作者指东说西。”(靖藏眉批略同)批者以王莽之典正是指“乱臣贼子”之流,“指东说西”不也正是“注彼而写此”吗?又如第八回写秦可卿“生得形容袅娜,性格风流”,甲戌本有夹批:“四字便有隐意。春秋字法。”而写秦可卿名字一段,甲戌本有夹批:“出名秦氏,究竟不知系出何氏,所谓寓褒贬别善恶是也。秉刀斧之笔,具菩萨之心,亦甚难矣。”写秦业一段,甲戌本有眉批:“写可儿出身自养生堂,是褒中贬。死后封袭(龙)禁尉,是贬中褒。”再如第四十五回,庚辰本有三处夹笔提到“春秋笔法”、“春秋字笔”。《红楼梦》正文第四十二回写薛宝钗把林黛玉以“母蝗虫”为喻讥嘲刘姥姥,就直接称之为“春秋的法子”。脂评还有“反面春秋”的批语,如第四十三回写贾母为王熙凤过生日凑份子,对众嬷嬷说:“这使不得。你们虽该矮一等,我知道你们这几个都是财主,分位虽低,钱却比他们多。”庚辰本有批语云:“惊魂夺魄,只此一句,所以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全是讽刺世事,反面春秋也。所谓痴子弟正照风自(月)鉴。若单看了家常老婆舌头,岂非痴弟子乎?”所谓“反面春秋”,是说《石头记》一书从反面写“春秋”大事,不能认为“一部书全是老婆舌头”而误以为是“家常老婆舌头”,而它“全是讽刺时事”,不能像贾瑞一类“痴子弟”只看正面而不看反面。总之,鞭挞丑恶、高扬美善、揭露奸邪、讽刺世事、嬉笑怒骂、皮里阳秋之笔,小说中在在皆是。
[九]史家之有曲笔:史家,指史臣、作史者,如董狐、司马迁等。曲笔:史家著史如实记载史实,直言无讳,此谓之直笔;而编史、记事有所顾忌或徇情避讳,不直书其事的谓之曲笔。后汉臧洪《答陈琳书》:“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戚氏所谓“史家之有曲笔”与前句“《春秋》之有微词”相对为文,故“曲笔”应包括下笔委婉曲折、微文讥讽的意思。曹雪芹为了躲避当时残酷镇压文人而大兴的文字狱,他充分利用小说的特点,故意不暴露创作年限、故事发生的地点,隐晦地描写书中涉及的满汉风俗,故意混淆故事的时间概念,反复强调“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无朝代年纪可考”、“并无大贤大忠理朝政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总之,《石头记》“毫不干涉时世”。还为了迷惑统治者的眼目,突出小说的“荒诞不经”,作者选择了“不避讳”的写法。尽管如此,与作者关系密切、了解作者创作过程、看到过《石头记》全稿的脂砚斋、畸笏叟等批者却了解并深知曹雪芹的“狡狯笔法”,脂批中有大量批语点出了小说中的“史笔”、“微词”,说作者“狡猾之至”。后来的读者也自然能够明白作者的用意,如二知道人就有评语说:“《红楼梦》妙处,又莫如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周振甫先生还指出第八回书中所写的“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灵真境界,幻来污浊臭皮囊。好知运败金无采,始叹时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一诗,乃是一首包含有“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残酷的政治迫害”内容的“政治诗”。
[十]绎:陈述。《尚书•君陈》:“庶言同则绎。”此句表明以下诸句乃分说。
[十一]写闺房……已满纸矣:雍肃,即“雝雝肃肃”的缩语,语出《诗•周颂•雝》:“有来雝雝,至止肃肃。”雝,同雍。《群书治要》本正作“雍雍”。雍肃,本指和谐严肃,这里指雍穆整肃,与下文“艳冶”义相反。艳冶,艳丽。梁庾肩吾《长安有狭斜行》:“少妇多艳冶,花钿系石榴。”《乐府诗集》卷三十五作“妖艳”。戚氏意谓,小说描写闺房虽然表面上写得雍穆整肃,似乎是“诗礼簪缨之族”,但是“闺房”之内的艳冶之象充盈于全书。第五回对秦可卿闺房的描写即属此例:
说着大家来至秦氏房中。刚至房门,便有一股细细的甜香袭人而来。宝玉觉得眼饧骨软,连说“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时,有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两旁有宋学士秦太虚写的一副对联,其联云:
嫩寒锁梦因春冷,芳气袭人是酒香。
案上设着武则天当日镜室中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连珠帐。宝玉含笑连说:“这里好!”秦氏笑道:“我这屋子大约神仙也可以住得了。”说着亲自展开了西子浣过的纱衾,移了红娘抱过的鸳枕。
作者在这里罗列了数种与古代香艳故事的风流韵事有关的器物,渲染出秦可卿房中陈设的华丽秾艳,这十分符合秦氏“擅风情,秉月貌”的特性。脂评于此有批语云“进房如梦境”,“艳极,淫极。已入梦境矣”,“设譬调侃耳。若真以为然,则又被作者瞒过”。钱锺书先生指出:“倘据此以为作者乃言古植至晋而移、古物入清犹用,叹有神助,或斥其鬼话,则犹‘丞相非在梦中,君自在梦中’耳。”又如第六回写凤姐闺房,先从刘姥姥眼中写出:“上了正房台矶,小丫头打起猩红毡帘,才入堂屋,只闻一阵香扑了脸来,竟不辨是何气味,身子如在云端里一般。满屋中之物都耀眼争光的,使人头悬目眩”;接着又从周瑞家的视角写道:“只见门外錾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儿家常戴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脂评于此有批语云“是写府第奢华,还是写刘姥姥粗夯?大抵村舍人家见此等气象,未有不破胆惊心,迷魄醉魂者。刘姥姥犹能念佛,已自出人头地矣”;“一段阿凤房室起居器皿,家常正传,奢侈珍贵好奇贷(货)注脚。写来真是好看”。紧接第七回又写贾琏“戏”熙凤,而“戏”的内涵则写得很含蓄蕴藉:周瑞家的“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凤姐房中门槛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忙蹑手蹑足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姐儿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奶子摇头儿。
正说着,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脂评有一长批:
妙文奇想,阿凤之为人岂有不着意于风月二字之理哉?若直以明笔写之,不但唐突阿凤身价,正亦无妙文可想。若不写之,又万万不可。故只用“柳藏鹦鹉语方知”之法,略一皴染,不独文字有隐微,亦且不至污渎阿凤之英风俊骨。所谓此书无一不妙。
余素所藏仇十洲《幽窗听莺暗春图》,其心思笔墨已是无双,今见此阿凤一传,则觉画工太板。
凡此描写,均表明贾府雍容华贵的背后是何等的妖艳污浊,焦大之骂又是最好的注脚。
[十二]状阀阅……已盈睫矣:阀阅,亦作伐阅,指豪门世家。秦汉功有五品:勋、劳、功、伐、阅,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这里指贾府。丰整,富饶齐备,与下文“式微”义相反。式微,衰败,语出《诗•邶风•式微》:“式微式微,胡不归?”朱熹《诗集传》:“旧说以及黎侯失国,而寓于卫,其臣劝之曰:‘衰微甚矣,何不归哉?’”盈睫,满眼。二句言贾府表面上豪华富有,但已经满眼都有衰败的迹象,正是冷子兴所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石头记》就通过贾府人参的有无多寡,象征贾府命运的盛衰起伏,周瑞家的所言人参“这东西与别的不同,凭是怎样好的,只过一百年后,便自己就成了灰了”,即用隐喻式的语言揭示出贾府的腐朽衰败。
[十三]写宝玉……不减历下琅琊:宝玉之淫与痴,书中有交代,第五回写警幻仙子对宝玉说:“吾所爱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其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第二回贾雨村论宝玉一类人说:“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宝玉“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直至“情不情”而弃家为僧;他“爱博而心劳”,其探晴雯、诔晴雯的情节描写,仅次于宝黛关系,其他如对金钏(三十回、四十三回)、平儿(四十四回)、香菱(六十二回)、龄官(三十六回),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他对女子的同情、爱怜、多情。试问“开辟鸿蒙,谁为情种”?是宝玉,正所谓“千古情人独我痴”(第五回)。历下、琅琊:典出晋王戎、王羲之故事。历下,古城名,在今山东历城县西。琅琊,郡名,在今山东胶南诸城一带。《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王氏出自姬姓……避秦乱迁于琅琊,后迁临沂。”历下、琅琊,均在山东,故连带及之耳。王戎多情,《世说新语•伤逝》载:“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晋书•王衍传》作王衍事)王羲之善悟,《晋书》本传载其三事,一是劝谏殷浩与桓温和谐,又曲止北伐,“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诫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为姚襄所败”。二是劝谏谢万,“万后为豫州都督,又遗万书诫之曰:‘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府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至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用,果败”。三是为国家前途深谋远虑,其上疏云:“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
国家之虑深矣,常恐伍员之忧不独在昔,麋鹿之游将不止林薮而已”。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即赞曰:“逸少早识,善察百年。”宝玉之善悟,书中有大量的描写,如抓周、续《庄子》、诔晴雯、化灰化烟等,正如鲁迅先生所评:“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属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遣,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
[十四]写黛玉……不啻桑娥石女:妒而尖,嫉妒而尖酸。不啻,不但、不止。桑娥,指汉乐府《陌上桑》所写的采桑女子秦罗敷。《方言》卷一:“娥、嬴,好也。秦曰娥。”《陌上桑》所写的秦罗敷貌美、聪明而忠于丈夫,她通过夸夫巧妙地拒绝了五马太守的调戏、勾引。石女,指望夫不得、痴化为石的贞女。《初学记》卷五引刘义庆《幽明录》:“武昌北山有望夫石,状若人立。古传云:昔有贞妇,其夫从役,远赴国难,携弱子饯送北山,立望夫而化为立石。”而吴世昌先生指出“石女”指石崇舞女绿珠。他在《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之注中指出:“‘石女’,指石崇家的舞女绿珠,殉石崇,坠楼而死。”考《晋书•石崇传》载,石崇被捕时“谓绿珠曰:‘我今为尔得罪。’绿珠泣曰:‘当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楼下而死”。亦可通。黛玉之妒而尖,小说写得非常突出,她不止一次地讥讽过宝钗,语言比刀子还厉害;恼怒过湘云,打趣过惜春,揭穿过
忙于夜赌的老婆子……她对宝玉的爱是纯真而自私的,真可谓“笃爱深怜”,“金玉良缘”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因此,她对宝钗的嫉妒尖酸尤为不顾一切,如第八回的回目就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内中写雪雁送手炉、黛玉谈冷热一节,即是明证;又如第二十九回回目下句为“痴情女情重愈斟情”,内中写黛玉听贾母、宝钗、宝玉谈到张道士派人送来的赤金点麒麟,探春说:“宝姐姐有心,不管什么他都记得。”黛玉冷笑道:“他在别的上还有限,惟有这些人带的东西上越发留心。”“宝钗听说,便回头装没听见。”这也是佳例。
[十五]他如摹绘……不可得也:玉钗金屋,指美玉金钗等饰物和楼台亭阁等建筑。金屋,极言屋之华丽,语出班固《汉武故事》:“胶东王数岁,(长)公主抱置膝上,问曰:‘儿欲得妇否?’长公主指左右长御百余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娇好否?’笑对曰:‘好。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长主大悦,乃苦要上,遂成婚焉。”芗泽罗襦,语出《史记•滑稽列传•淳于髡传》:“罗襦襟解,微闻芗泽。”芗泽,即香气。罗襦,这里指华丽的服饰。靡靡,富丽而华美,语出司马相如《长门赋》:“间徙倚于东厢兮,观夫靡靡而无穷。”《文选》唐吕向注:“靡靡,室宇美好也。”戚氏意谓《石头记》在描摹贾府豪华阔绰富贵气象方面,已经达到了令人心荡神怡的境地,但其中却没有“一字一句”粗鄙猥亵的语言。这是符合《石头记》的实际描写的。《石头记》虽然“深得《金瓶》壸奥”,但它拒绝对色情污浊生活进行庸俗淫秽的自然主义描写,这在第一回就有作者的批判:“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因此,《石头记》具有一种“乐而不淫”的婉约风格。
[十六]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两对反义词。《左传•隐三年》:“骄奢淫泆,所自邪也。”孔《疏》:“淫,谓嗜欲过度;泆,谓放恣无艺。”“淫泆”同“淫佚”,也作“淫逸”。贞静,节操坚贞、性情淑静。《后汉书•曹世淑妻传》:“清闲贞静,守节整齐。”双管齐下,语出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五《张璪》:“唐张璪员外画山水松石,名重于世,尤于画松,特出意象,能手握双管,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干,势凌风雨,气傲烟霞。”戚氏引用“双管齐下”之典旨在强调《石头记》叙事写人的技巧远远超过了“一声两歌,一手二牍”的水平,达到了一石三鸟、多管齐下的境地;“不啻”者,“不止”之谓也。是极赞《石头记》的高超技巧已无以复加。
[十七]盲左、腐迁:指左丘明、司马迁。戚氏把《石头记》的作者同史学家左丘明、司马迁相比,这是十分精辟的见解,其要义有二:第一,提出了小说与史书的传承关系问题,看到了史传中蕴含有小说因子和小说向史传文学汲取养料这一重要现象。同戚氏一样,明清小说评点家如金圣叹、李卓吾、张竹坡、毛宗岗等人也不时把所评点的小说与《左传》、《史记》相提并论,对此,钱锺书先生有精辟的分析:“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汀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中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第二,似已感悟到《石头记》的作者与盲左、腐迁一样是“翻过筋斗来的”,已经接触到了“发愤著书”的理论核心。戚氏自当对“盲左”之“盲”、“腐迁”之“腐”了然于胸,然其时他对《石头记》的作者是谁、经历如何并不深知,而能感悟至此,真正令人钦敬。
[十八]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两意,本指不同的命意。《宋书•选举志一》:“场屋之文,专尚偶丽,题虽无两意,必欲厘而为二,以就对偶。”这里指《石头记》由于运用了高超绝伦的艺术技巧叙事写人,因而它所描写的人物和故事迷离惝恍、真假难辨,往往可以使人得出正反两种认识,对此,戚氏提醒读者应当努力抓住作者的创作主旨和小说的基本倾向,这样才有可能“得作者微旨”,“得此书弦外音”。作者本人深深致慨:“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企盼后人能辨味外之味,能识弦外之音;脂批也多次对“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写有批语“此书表里皆有喻也”,“凡看书者从此细心体贴,方许你看,否则此书哭矣”;“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应当说,戚蓼生的这种见解对今天的红学研究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索隐派红学的历久不衰从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一点。
[十九]譬之绘事……幽处不逾一树:绘事,绘画之事。《论语•八佾》:“绘事后素。”石有三面、路看两蹊,语出五代后梁画家荆浩《画山水赋》:“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豆人。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皴,隐隐似眉,远水无波,高与云齐,此其诀也。山腰云塞,石壁泉塞,楼台树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有两蹊,水看岸基,此其法也。”戚氏是借绘画理论进一步比喻《石头记》内涵复杂,读者须抓住要领,紧盯“佳处”、“幽处”去阅读;如何才能紧盯“佳处”、“幽处”而不失之片面偏颇呢?画石者以“一峰”表示,画路者以“一树”楬橥,金针度人之意显而易见。戚氏此论是从古人绘画强调“神韵”而来,古人之论“神韵”夥矣,不烦赘述,兹引钱锺书先生妙说作一总结:“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余地,耐人玩味,俾由所写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曰:‘取之象外’,曰‘略于行色’,曰‘隐’,曰‘含蓄’,曰‘景外之景’,曰‘馀音异味’,说竖说横,百虑一致。”
[二十]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画天花,但闻香气:捉水月,语出《景德传灯录》卷三十:“镜里看形见不准,水中捉月争拈得。”佛教以水中之月
喻诸法(一切事物)之无实体,大乘十喻之一。《智度论》卷六:“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化。”后泛指一切虚幻的景象。水中捉月,结果可知,故曰“争拈得”?戚氏借以比喻读者不能为书中的幻象所蒙蔽,去做捉月水中之事,应当拨开幻象去抓住书中的真谛(“只挹清辉”)。雨天花,语出《维摩诘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大人闻听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本以花着身不着身验证诸菩萨的向道之心,若结习未除,花即著身。戚氏同样借以比喻读者要抛开令人眼花缭乱的幻象(天雨香花),用所具之“一心”去欣赏作品的精华(“但闻香气”)。这两个佛教典故用得非常贴切,对读者很有提示指导作用。无独有偶,《红楼梦》第十七回至十八回有正本回末总批云:“此回铺排,非身经历,开巨眼,伸大笔,则必有所滞罣牵强,岂能如此触处成趣,立后文之根,足本文之情者。且借象说法,学我佛阐经,代天女散花,以成此奇闻妙趣。……”戚氏或许受启于此。
[二十一]弦外音:比喻语有含蓄,言外别有不尽之意。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来。”
[二十二]未窥全豹:语出《世说新语•方正》:“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蒱,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戚氏借以喻《石头记》非完帙。
[二十三]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此二句仍借佛教理论对小说的情节发展做出评论。回环,义近轮回、因果循环,盖指贾府由盛至衰的历程。万缘,佛家指一切因缘,即事物的因果关系。幻泡,即梦幻泡影,佛经上讲,世上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无常,一切皆空,如同梦境、幻术、水泡和影子。《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应化非真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戚氏借喻小说所流露的世事虚幻、人生短暂的基调。
[二十四]作者慧眼婆心……便具无数慈航矣:慧眼婆心本为佛家语,这里指作者敏锐的眼力和慈爱的用心,是对作者才华和写作目的的称颂。转语,佛教语,禅宗谓拨转心机,使之恍然大悟的机锋话语,对答的一方要根据自己的体会作一简短的转释,谓之“下转语”。戚氏借以喻《石头记》八十回以后的内容。慈航,佛教称佛以慈悲之心度人,使脱离苦海,有如航船之济众。萧统《昭明太子集》卷二《开善寺法会》诗:“法转明暗室,慧海度慈航。”在戚氏看来,《石头记》前八十回已经大致写出了人和事的盛衰回环,点明了世事虚幻、人生短暂的主旨,读者只要凭着自己的诸多悟解,就可以推知书中人、事的结局了,而不必“以未窥全豹为恨”,因为你的诸种领会完全可以使你脱离悲伤的心境而趋于平静,就如同佛家以慈航之心度人,使众人乘船脱离苦海一样。这是对《石头记》非完帙而极具价值的一种折中的看法。
[二十五]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刻楮叶,语出《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列子•说符》亦载,文字小异。)后以此典形容技艺高超,也用以指费时费功、徒劳无益之事。王安石《莫疑》:“莲花世界何关汝,楮叶工夫浪费年。”戚氏用以隐指程、高等人的续书乃徒劳无益。彼,即指程、高。周汝昌先生认为戚氏撰写此文时,已经得知程、高“全本”已在刊印,所以语存讥刺:“戚本原钞本入于戚蓼生的年代,上限仍应在乾隆三十四年,下限则可推到最晚为五十六年。……戚本之购买、作序,甚至可能包括往外传抄,都还是在程本印行之前的事情。”可以参考。在戚氏看来,续书者沾沾自喜而实际上是做了徒劳无益之事,他们同“开卷而寤者”相比差得甚远。
[二十六]德清戚蓼生晓堂氏:《红楼梦大辞典》“戚蓼生”条云:“字晓圹,浙江德清人,生年不详。据《德清县续志》等史籍记载,他是乾隆二十七年(1762)举人;三十四年进士;三十九年以户部主事充任四川乡试副考官;四十七年出任江西南康知府,不久擢升福建盐法道;五十六年为福建按察史;五十七年(1792)‘以劳悴卒官’。”邓庆佑先生对戚蓼生的家世和生平有较详细的考证,并考证出其生年为“乾隆四年(1739)”,卒于乾隆“五十七年的可能性更大”。
【相关文章】
本文地址:http://www.yesbaike.com/view/144857.html
声明:本文信息为网友自行发布旨在分享与大家阅读学习,文中的观点和立场与本站无关,如对文中内容有异议请联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