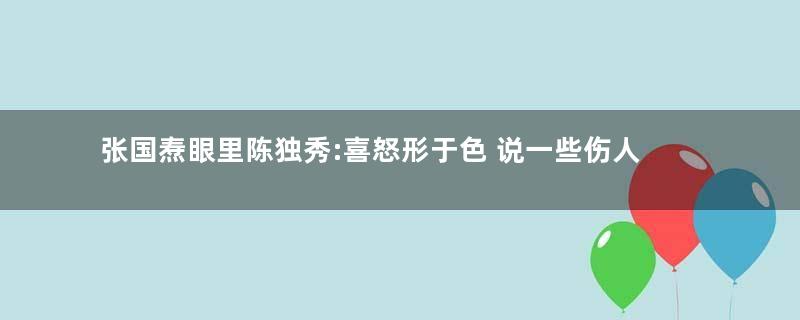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与文学的发展史,是两条不同线。认识每一条线,都不能孤立地看,参照起来,就可以窥见一些问题。在这里,把鲁迅和陈独秀对比起来,就可以摸到一些线索的。不过,打量这些线索,也该扩大一些眼界。比如陈独秀的命运,何以会如此,他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坐标。在这坐标里,我们环视周围的环境,是也有惊人的发现的。
我有时想陈独秀的苦运,也连带记起他的学生、曾做过共产党的高官的张国焘。张氏生于1897年,1916年10月到了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到北京几个月后,陈独秀才出现在校园中,任文科学长,论辈份,张国焘自然属于学生。他虽不在文科,是理工预科的新生,但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最先拥护的人员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算是发起人,后来因之而被捕。和陈独秀一样,由新文化的倡导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张氏晚年曾著有《我的回忆》,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章,资料很是可贵。比如记叙陈独秀出狱的文字,就画出了当时的氛围,陈氏的英杰式的仪表跃然纸上: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再没有回到北大。
陈独秀与张国焘,按天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的环境却让他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而转向政治。这一转向和胡适的政治热情不同,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了学人身份,甘愿做一个革命者。把五四的文化风潮,从书斋转向社会的内部。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沉重的现实不会让这样的学人沉到书本的深处,他们急于改变一种社会现状,革命才是重要的。《新青年》的另一类人如周作人、钱玄同就没有类似的冲动,他们觉得梳理旧物,引进新学,大量翻译域外学术,培养新的文化土壤,似乎更为迫切。历史的轨迹后来是这样的,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前者,惟有京派的几个少数人,却恪守了学术的园地。一向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读书人,还像孔夫子所说的,有献身社稷的悲壮。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过陈独秀,他后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它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彼此有着相近的血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的巨大引力,是别一民族与国度无法相比的。
陈独秀最初组建共产党,就已意识到像国民党那样的党魁制是有问题的。解决它的办法,应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经过五四民主之风洗礼的他们,在思想深处就一直有着读书人的特点,存在一个基本的底线。问题的复杂性是,当他们投身于自己钟情的事业的时候,周围布满了种种陷阱,有时不得不被推向一种两难。背后是共产国际,身边多稚气的热血青年,以及各类机会主义者。在严峻的事实中,便不免有权力之争、党风之变。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感到“权力、组织、一致、领导”存有非人性化的因素,他们自己也在制造着这些东西。选择的悖论,是五四后知识界普遍碰到的问题。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多次暗示了此一点。后来所以脱党,走了另一条道路,有着十分深切的原因。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有些描写十分精彩。个性与气质飘然于纸上。顺着他的思路,当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境况。张氏每每写到这位前辈,都有敬重之笔。偶有批评,语气亦十分中肯,没有漫画的笔法。这些印象都是自然流露出的,显然无雕刻的痕迹,解读的过程里,可以嗅出别一类文章中鲜见的气息。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大概就可以托现出来了。
在张国焘的眼里,陈独秀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他不太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于承认,是有气魄的。建党初时,其身上还有些民主作风,让人有一种信任感。
此后中国革命一波三折,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农民运动中的流寇问题,使其渐渐感到早期设想的蓝图,已多难实现了。革命正在向相反的路途滑进,荆棘日多。不仅陈氏不能适应,张氏也苦楚难排,多积淤于胸。此一体验,后来的几代有知识分子色调的党内人士,都有一点的。《我的回忆》对陈独秀的把握,是建立在书生的基点上,并无政客的一面。张国焘写道: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应当说,早期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寻路而有了一个路向,自愿地加入到一个行列里。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旧世界的遗风,俄共的习气都交织其间,知识界自然与其发生冲突。国共合作的时期,陈独秀就已经感到了其间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味地让共产党消融在对方之中。独立性的存在就可疑了。张国焘的回忆录不止一次地记录了陈独秀的发脾气、愤怒和焦虑,因为他判断的事情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迥异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时候他感到了党内独立见解的不易确立,个人的真实感受成了罪过。连瞿秋白这样文人气的人,在掌权之时亦带有片面的、伤害他人的一面。政党机器的运作过程,反将个体的人血肉之感抹杀掉了。张国焘这样写道: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如果不是作者记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不会懂得事态的严峻性。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人的书斋里的设想,大多要破灭的。创立过五四独立精神的人,现在面临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存在。陈独秀被撤掉职务之后,共产国际就已经意识到这位前任总书记潜在的破坏力。俄国的托洛茨基不是被铲除了么?那原因是他有了异样的声音,不协调了。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希望有多样的声音,因为那时面临的黑暗过于强大,统一性、共同性要远远重于分歧性、个性。斯大林就担心陈独秀会不会另组一个政党,那样的话,中国革命就完全混乱。张国焘有一次见斯大林时,就被问到了这一点:
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档案,不再成为机密,人们终于可以窥见其中的讳莫如深的存在了。回望那一段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端。最倡导自由的人,一生都置身于非自由的环境中;为大众殉道的寻路人,却被大众的冷眼所视,收获的只是悲凉的苦果。文学家们描述那一段历史,诗的成分过多,不得要领。瞿秋白已经很是人性化的人物了,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得不做一些背理的事。至于陈独秀、张国焘也难逃劫运,一生之中做过许多错事。那一代人是经历大痛苦的,所从事的事业,越走越远离了自我。几十年过去,却发现漫长的跋涉,并无彼岸,迷津四布,反而不及起点时那么目标清醒。世间的道理,唯有体验过生活的人,才最为清楚,在象牙塔里永远感受不到这些的。体验中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这是那一代人给我们的馈赠。未经历于此的人,事前向其述说而无用。待到事后,又无可如何。大家都在这样可怜的世间。
张国焘与陈独秀在晚年都放弃了政党事业。在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失败者。关于他们的批判文章和图书,已很是不少。作为一种现象,在讨论二人的历史时,以成败论英雄未必正确。问题在于,政治失败了的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胜利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其中引发出的教训是什么?张国焘的情况十分复杂,世人对其有好感者不多,暂且不谈。仅陈独秀带给后人的遗产,是丰沛的。他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了自己的家园?难道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这是现代史的一个黑结,它解开了,也许历史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相关文章】
本文地址:http://www.yesbaike.com/view/135751.html
声明:本文信息为网友自行发布旨在分享与大家阅读学习,文中的观点和立场与本站无关,如对文中内容有异议请联系处理。